听书 ▏太图网上读书会·第777期《目光》2
2021年04月13日 10:13:23
作者简介:
陶 勇
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眼科学博士。现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导,葡萄膜炎与眼底病专家。
李 润
原名李光辉,山西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北京理工大学硕士,曾任TCL集团、华孚集团品牌总监,“80后”新锐后现代作家,歌词创作人。
内容简介:
《目光》是一本医生的沉思录,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启示录。书中包含了陶勇从医二十年来对人生的思考与感悟,对生死的看法,对人性善恶的思辨,对放弃与坚守、少数与多数的选择,对医患关系的审视……
他的文字就像是他的手术刀,将人间种种悲欢都精准而细腻地在窄小的纸面上铺开、沉淀,他想治好每个人的病,也想医好每个人的心。虽然被伤事件迫使他的人生转变了方向,但是他一直坚持的以仁心做事的信仰,从未改变。
事后我才知道,当时我医院的院长和同事第一时间都在为救我而奔跑着,这期间,几位医师同院领导商量了手术方案,开始进行各处伤口的缝合与处理。我的左臂与左手受伤最为严重,神经、肌腱、血管两处断裂,手外伤专家陈主任,果断做出了救治方案,手术持续了约七个小时。
我的妻子也从新闻上看到了消息,通知了我的父母,两位老人坐地铁来到医院,我可以想象他们的心情是何其恐慌。
我醒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的中午,麻药的药劲儿还未散去,整个人晕晕沉沉,不知身在何方,只觉得脑袋像被套了一个坚硬的铁壳,勒得我头痛欲裂。
等再次清醒,我才慢慢恢复意识。我躺在ICU(重症监护病房),头上缠满纱布,身体被固定在床上。透过白色纱布的缝隙,我看到我的两条手臂被套上坚硬的石膏,身体一动不能动,头顶上方挂着输液吊瓶,药水不紧不慢地滴落。
这些,是在我之前的二十年中太过熟悉的场景,而今天我才有机会特别认真地观察——原来白色的屋顶上有几个黑色的斑点;明黄的白炽灯照得整个房间通明空旷;输液管里的滴液,先是慢慢凝聚,然后形成一颗结实的水滴,挣脱管口的约束重重地滴下,悄无声息地流入我的身体。
我无数次见过躺在ICU的病人,知道他们的痛苦,更懂得他们求生的欲望。然而,当我自己实实在在地躺在这里,才真正刻骨地体会他们的感受。
我为什么会躺在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父母、妻儿他们在哪里……我通通不得而知。
我被剧烈的头痛折磨着,也无暇思虑更多。这种疼痛不像平时的疼痛有清晰的位置来源,而是一种又涨又晕、仿佛是一团黑云死沉死沉地压在头上的感觉。后来听护士说,那时我的头肿胀得比平时看起来大了一倍。
这种疼痛让我如在炼狱,这是一种持久的、完全没有缓解意向的疼,我全身心地同疼痛做着斗争,只觉得时间过得异常缓慢。
一直到第三天,我的状况才渐渐好转,同时也得到了各方的慰问。只是此时我呼吸困难、气力微弱,也难以表达太多。杨硕大夫在被抢救后也被安排在了病房,他放心不下我,偷偷跑过来看我。我看到他头上的纱布,心里痛楚,想流眼泪,但似乎连流泪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们就像一起经历了生死的战友,目光相对,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
主治大夫告知我我已脱离生命危险,让我放心。事实上,我还没有想到这个层面,疼痛让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睡过去。
迷迷糊糊中,我看到妻子来了,她没有我想象的那样悲伤,就好像我们平时见面一样。她甚至笑着对我说:“你知道吗,你都上微博热搜了。”这个傻姑娘,这句话也真是符合了她的性格,大大咧咧、简单直接。我苦笑了一下,特别想问她家里的情况,可是此时我完全没有力气开口。她好像知道我要问什么,柔声地告诉我,女儿暂时拜托朋友照顾,父母也安顿好了,一切都好,让我放心。我心酸不已,但也动不了,只能向她眨了眨眼。我能想象家人们是经历了一场多么大的震荡,妻子红红的眼眶还是出卖了她的乐观,我知道她一定是昼夜未眠、哭了很多次。ICU不能久留,妻子陪我聊了一小会儿便被请了出去。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头痛仍在持续地折磨着我。我终于知道,原来被利器所伤,第一时间的感觉竟然并不疼,而恢复的过程才是疼痛的高峰。头疼是脑水肿造成的,我整个脑袋疼得像是扣了一个完全不透气的钢盔。但我知道这个过程谁也帮不了我,我只能靠自己一点点扛下去。
一直到第五天,我的头痛终于有所缓解,我清晰地感觉到了疼痛的位置。但我感到噬骨的寒冷从左臂传来,我惊惧是不是我的左臂已经不在了。直到大夫说手术很成功,我才知道神经和肌肉全部被砍断,缝合后还没有知觉,需要时间去修复,这才让我稍微的放下心来。
有了意识后,我开始有了身体的运转需求,我知道,这时候我必须多进食一些,才能加强康复效果,于是接下来的每顿饭我都尽量勉强自己多吃几口。
第六天,我又渴望又害怕的便意来了,我托护士帮我找了一位男护工搀扶我走进卫生间。那是我受伤后第一次下床,身体好像不是自己的,我完全控制不了它。护工用了好大的力气才勉强扶我迈出一小步,病床距卫生间大概也只有三十米的距离,但它好像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路程。在勉强排了一次便后,我心中有些愉悦,仿佛终于看到了一点点曙光——身体战胜了病痛,它会越来越好。
从医生瞬间变为患者,第一时间我想到的就是那些眼病患者是怎样过来的。我眼前出现最多的也是那些盲童的影子,他们家境并不富裕,甚至可以说一贫如洗,但是也一直坚持,从未放弃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疼痛在各位医师和护士的护理下一点点缓解,头上的水肿消退,但是伤口的痛开始立体清晰起来。甚至由于根本无法入睡,不得不吃一些止痛药才能睡得安稳。
我右手的伤势相对较轻,已经拆除了石膏,露出了可怕的伤痕,红红的,缝合线像一条蜈蚣一般趴在那里,四十多针,足足有十几厘米长。左臂依然没有知觉,我开始感到有些焦虑和担心,我不敢想象假如失去了左手,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现在我甚至连上个卫生间、洗个脸都会变得很费劲——可还有好多患者在等着我做手术,我是否还能继续此生热爱的医疗事业呢?
扫描下方二维码直接登录“太图之声”手机版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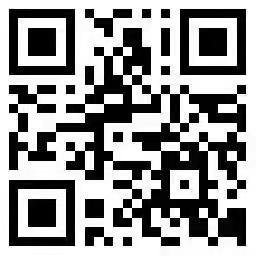
往期回顾:2021年太图之声









 返回顶部
返回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