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书 ▏太图网上读书会·第809期《我心归处是敦煌》4
2021年05月27日 16:10:59
作者简介:
樊锦诗
1938年生,浙江杭州人。生于北京,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1963年毕业后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至今。
曾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院长;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共十三大代表,历任第八至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顾春芳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宝山人,来自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院。主要研究领域为艺术学、戏剧戏曲学、戏剧美学、电影学。主要学术著作有《呈现与阐释》、《戏剧学导论》、《她的舞台》、《戏剧交响》等,出版诗集《四月的沉醉》。
内容简介:
本书独家收录了一批从未公开过的资料,展现这位传奇女性的志业与爱情、困境与坚守,解读敦煌艺术崇高之美,历数百年敦煌学研究的筚路蓝缕,披露莫高窟“申遗”及“数字敦煌”背后的故事。
外界都认为我留在敦煌是自己选择的。说实话,其实我有几次都想离开敦煌。但是为什么留下来,这是一个人的命。
20世纪60年代的莫高窟和今天的莫高窟不可同日而语,那时的敦煌人都是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虽然我大学时就习惯了独立生活,但起初还是不能完全适应敦煌的生活。在这里,吃得最多的菜是“老三片”,土豆片、萝卜片和白菜片。春天最好吃的食物,就是榆树上结的榆钱。因长期营养不良加上过度劳累,有一次我竟然晕倒在办公室。
研究所绝大多数人员都住在土坯平房里,直到1980年,国家才给拨款修建了新的宿舍楼。当时的整个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和外界联络非常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周围根本没有商店,有了钱也没有地方可以买到东西。
整个莫高窟直到1981年才通上电,在此之前的几年一直自己发电,每天只能保证两三个小时的用电,根本不能像在学校那样,到了晚上还可以到自习室去学习。
治沙和种树,是当时研究所所有人都必须参加的两项工作。保护石窟、防沙治沙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种树。种树的事情从冬天就开始酝酿,一到开春就马上栽下树苗。这里最好活的树就是杨树,现在围绕莫高窟蜿蜒的参天大杨树,都是当年的莫高窟人一棵棵亲手植下的。
西北的生活,使我逐渐忘记了都市,忘记了一切和城市有关的生活,忘记了我也曾是“南国女儿”。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倾注在工作中。
如果说我从来没有犹豫、没有动摇过,那是假话。敦煌和北京、上海相比,确实是两个世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感到孤独。尤其到了春天,整天整天地刮风,窗外刮风屋内下沙。我常常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把我给忘了,不止一次偷偷掉眼泪。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进石窟,我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适应了敦煌的生活。随着我对敦煌石窟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入,我也逐渐对敦煌产生了割舍不断的感情。我之所以最终没有离开,其中固然有命运的安排,但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从情感上越来越离不开敦煌。而最终让我安下心来,心无旁骛地守护敦煌,还是要感恩我的先生老彭。
我和老彭是大学的同班同学,1967年1月15日,我和老彭(彭金章)结婚了。婚后,他在武汉,我在敦煌,我们只能经常通信。我感觉他对我非常关心和体贴,是个可靠、有情的丈夫。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无话不说,我们不在一起的时候也会经常交流,但我们说的都不是家庭琐事,主要谈的都是各自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时,我父亲刚刚含冤而死,大弟因为父亲的原因不能落实工作,母亲又病倒了,偏偏在这个时候自己又怀孕了。我觉得自己身心疲惫,精神上的紧张和巨大的悲痛,导致我有流产的迹象。经过及时治疗,才幸运地保住了孩子。那时候,最强烈的念头就是离开敦煌,到武汉去。然而,在动荡时期,是无法解决分居问题的。我们想调到一起,也只是天真的幻想而已。
随着时间的推移,“十年动乱”已告结束,到了解决分居问题的时候了。老彭当时急切希望我尽快调往武汉,但甘肃和武汉大学两方面的组织都坚决不放人,双方争持了很长时间。1986年,老彭最后做出了调来敦煌的决定,我们一家才终于团聚了,老大都念高中了,老二也念完小学了。我有一句话跟好多人说过,我说我们家的先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一般的家庭都会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最终散了。但是他为我做了让步,放弃了自己热爱的事业,也放弃了自己亲手创立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
遇上了老彭这样的好人,是我一生的幸运。
到了敦煌后,老彭放弃了商周考古的教研事业,改行搞了佛教考古。他主持了莫高窟北区石窟两百多个洞窟的清理发掘工作。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是研究所成立四十多年以来想搞清而没有搞清的问题。老彭很热爱这个工作,一跟人说起北区,就兴奋得停不下来。如果他的价值因为来到敦煌而得不到实现的话,我一辈子都会感到内疚,好在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事业。
他1988年开始北区石窟考古工作的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六十多岁以后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报告,他除考古报告外,还写了不少文章,还当了《莫高窟北区考古论文集》的主编,这本论文集后来在中国香港、法国都出版过,有一定影响。
老彭这一生不容易。小时候家境贫困,是兄嫂带大的;娶妻生子,两地分居,家也不像个家;自己开创的考古专业为了我而中途放弃;还没等享受天伦之乐,晚年又得了直肠癌。
我知道他一直在和病痛做斗争,我能做的就是请大夫想办法,缓解他的痛苦。我心里明白,他正在一天一天慢慢离我们远去,直到最后看不见。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想各种办法,好好护理他,不让他受更多的罪。2017年7月29日,老彭走了。
一个月后,我又回到了敦煌。一切都是老样子,只是我的老彭不在了。
扫描下方二维码直接登录“太图之声”手机版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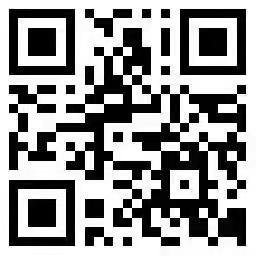
往期回顾:2021年太图之声









 返回顶部
返回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