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书 ▏太图网上读书会·第929期——《相约星期二》4- 教室
2021年11月11日 15:46:01
编辑撰稿人·播讲人
赵美华
太原市图书馆信息部馆员
作者简介
米奇·阿尔博姆,美国专栏作家、电台主持、电视评论员。代表作有:《相约星期二》、《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一日重生》、《来一点信仰》、《时光守护者》。
内容简介
年逾七旬的社会心理学教授莫里在1994年罹患肌萎缩性侧索硬化(ALS),已时日无多。作为莫里早年的得意门生,米奇每周二都上门与教授相伴,聆听老人最后的教诲,并在他死后将莫里·施瓦茨教授的醒世箴言缀珠成链,冠名《相约星期二》。
死亡既作为该作品的主题,又作为该小说的线索,传递了作者对于人生更深入、更透彻的思考。
阳光从餐厅的窗户射进来,照亮了房间里的硬木地板。我们在那儿已经谈了近两个小时了。常有电话打来,莫里让他的助手康尼去接。
康尼把所有打电话来的人的名字记录在莫里那本黑封面的小登记簿上:朋友,默念师,讨论小组,想为某本杂志给他拍照的摄影师。
显然,我不是唯一有兴趣访问他的人——“夜线”节目使他成了名人——但我还是对他有那么多的朋友而感到惊讶,甚至还有些忌妒。
“你知道,米奇,因为我是个快死的人,所以人们才对我感兴趣。”
“您一直是个有趣的人。”
“啊,”莫里笑了。“你真好。”
不,我并不好,我心里在想。
“原因在于,”他说,“人们把我视为一座桥梁。我不像以前那样活着,但我又没有死……我类似于… …介于两者之间。”
他咳嗽起来,随后又恢复了笑容,“我已经踏上了最后的旅程——人们要我告诉他们该怎样打点行装。”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待我这么热情。我几乎已经与十六年前与他告别的那个有出息的学生判若两人。如果没有“夜线”节目,莫里也许到死也不会再见到我。对此我没有任何正儿八经的理由,除了人人现在都会找的借口。我一心一意关心着自己的生活。我很忙。
我怎么啦?我问自己。莫里尖细、嘶哑的嗓音又把我带回到了大学时代。我那时视有钱为罪恶,衬衫加领带在我眼里简直如同枷锁,没有自由、貌似充实的生活——骑着摩托,沐着清风,游逛巴黎的街市或西藏的山峦——并不是有意义的生活。可我现在怎么啦?
八十年代开始了。九十年代开始了。死亡、疾病、肥胖、秃顶接踵而来。我是用许多梦想在换取数额更大的支票,只是我没有意识到而已。
莫里却又在谈美妙的大学生活了,仿佛我只是过了一个长长的假期。
“你有没有知心的朋友?”
“你为社区贡献过什么吗?”
“你对自己心安理得吗?”
“你想不想做一个富有人情味的人?”
我坐立不安起来,我的心绪被这些问题彻底搅乱了。我怎么会变得这样?我曾经发过誓,永远不为钱而工作,我会参加和平队,去美丽的理想乐园生活。
然而,我在底特律一呆就是十年,受雇同一个报社,进出同一家银行,光顾同一家理发店。我已经三十有七,比做学生那会儿更有能耐,整天泡在电脑、调制解调器和手机里。我专门写有关富有的运动员的文章,他们一般对我这样的人也是很在意的。我在同龄人中已不再显得稚嫩,不用再穿灰色的无领长袖衫或叼着没有点燃的烟来作修饰。
我的每一天都很充实,然而,我在大部分时间里仍感到不满足。
我怎么啦?
莫里在吃他的东西,这顿饭他已经吃了四十分钟。他手的动作显得有点笨拙,好像刚刚才开始学着用手。他不能用力地使用刀。他的手指在颤抖。他每咬一口食物都得费很大的劲,然后再咀嚼好一阵子才咽下去,有时食物还会从嘴角漏出来,于是他得放下手里的东西,用餐巾纸擦一擦。他手腕到肘部的皮肤上布满了老人斑,而且松弛得像一根熬汤的鸡骨头上悬着的鸡皮。
有一阵子,我们俩就这么吃着东西。一个是患病的老者,一个是健康的年轻人,两人一起承受着房间里的寂静。我觉得这是一种令人难堪的寂静,然而感到难堪的似乎只有我。
“死亡,”莫里突然开口说,“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米奇。可不幸地活着也同样令人悲哀。所以许多来探访我的人并不幸福。”
“为什么?”
“唔,首先,我们的文化并不让人觉得心安理得。我们在教授一些错误的东西。你需要十分的坚强才能说,如果这种文化没有用,就别去接受它。建立你自己的文化。但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他们要比我——即使在这样的处境里——更不幸。
“我也许就要死去,但我周围有爱我、关心我的人们。有多少人能有这个福份?”
他毫不自怜自哀的态度使我感到惊讶。莫里,一个不能再跳舞、游泳、洗澡和行走的人,一个再也不能去开门,不会自己擦干身子,甚至不能在床上翻身的人,怎么会对命运表现出如此的乐于接受?
我望着他费劲地使用着叉子,好几次都没能叉起一块番茄——那情景真令人悲哀。
然而我无法否认,坐在他面前能感受到一种神奇的宁静,就像当年校园里的清风拂去我心中的浮躁一般。
“你知道我会怎么死吗?”他问。
我扬起了眉毛。
“我会窒息而死。是的,由于我有哮喘,我的肺将无法抵御疾病的侵入。它慢慢地往上跑。现在它已经侵蚀了我的腿。用不了多久它会侵蚀到我的手臂和手。当它侵蚀到我的肺部时………”
他耸了耸肩。
“……我就完蛋了。”
“米奇,你不必害怕我的死。我有过美好的生活。我们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我或许还有四五个月的时间。”
他闭上了眼睛,摇摇头。“我的油箱已经空了。”
我有些紧张地做了个拍大腿的动作。该结束这个下午了。
“再回来看看你的老教授,”当我拥抱着和他道别时莫里说。我答应我会来的,这时我尽量不去想上一次我作出允诺的时刻。
几个星期后我飞往伦敦。我是去报道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的,那是世界顶级的网球比赛。
不知什么原因,我时常会想起莫里。我悲叹莫里来日无多的生命,同时又忌妒它的充实。
莫里,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建立了他自己的文化——早在他患病之前就这么做了。小组讨论,和朋友散步,去华盛顿广场的教堂跳舞自娱。他还制定了一个名叫绿屋的计划,为贫困的人提供心理治疗。
他博览群书为他的课寻找新的思想内容,他走访同事们,与毕业的学生保持联系,给远方的朋友写信。他情愿花时间去享享口福和赏玩自然,而从不浪费在电视喜剧或周末电影上。他建立了一种人类活动的模式——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爱护——这一模式充实着他的生活。
我也建立了我自己的文化:工作。我在英国做四到五份新闻媒体的工作,像小丑一样地跳来跳去。我一天在电脑上要花八个小时,把报道传送回美国;此外我还要制作电视节目,跟着摄制组走遍伦敦的每一个地方。我还要在每天的上午和下午主持听众来电直播节目。这份负担确实够重的。几年来,我一直将工作视为我的伴侣,把其它一切都抛在了脑后。
公开赛结束了,我关掉电脑,清理完工作台,回到了住处打点行装。已经是深夜了,电视里早已没有了画面。
我飞回底特律,傍晚时才到达。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一头倒在了床上。
醒来后看到的是一则爆炸性的新闻:我那家报纸的工会举行了罢工。报社关闭了。大门口站着纠察队员,请愿者在街上游行示威。作为工会的会员,我没有选择。我突然之间、也是我生活中第一次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支票,和老板处于对立面。
我感到既困惑又沮丧。虽然我在电视台和电台的打工是一份不错的副业,但报纸始终是我的生命线,是我生命中的氧气。当我每天早上看见我写的报道见诸报端时,我便知道,至少从某个意义上说我还活着。
现在它消失了。随着罢工的继续——一天,两天,三天——我所熟悉的生活方式被打乱了。原来每天晚上都有体育比赛需要我去采访,现在我只能呆在家里,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我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读者是非常需要我的专栏文章的,可我吃惊地发现,缺了我,一切照样进行得十分顺利。
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我拿起电话拨了莫里的号码。
“你来看我,”他的语调不像是询问而像是命令。
“我能来吗?”
“星期二怎么样?”
“星期二很合适,”我说,“就星期二。”
扫描下方二维码直接登录“太图之声”手机版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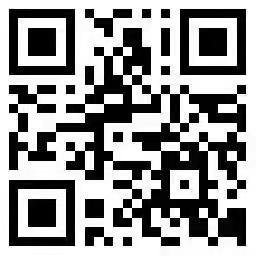
往期回顾:2021年太图之声









 返回顶部
返回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