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图之声(第1052)▏馆员讲书《巴黎记》2(可以听哦!)
2022年04月29日 15:15:57
编辑撰稿人
洪霞
太原市图书馆信息部馆员
播讲人
黄丽萍
太原市图书馆数字资源部馆员
作者简介
于坚
1970年开始写作诗歌、散文、小说、评论至今。
1980年开始摄影至今。
1992年开始拍摄纪录片至今。
著有诗集、文集多种。获数十种诗歌奖、散文奖。
长篇散文《印度记》获2012年《人民文学》杂志非虚构作品奖。
在第十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中,荣膺“2016年度杰出作家”。
纪录片《碧色车站》入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银狼奖单元。
系列摄影作品获2012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华夏典藏奖。
纪录片《同饮一江水》总撰稿。
最近二十年为《中国国家地理》《华夏人文地理》《旅行家》等刊物特约撰稿人。
在国内外多次举办摄影展。
内容简介
到巴黎去,这是一种世界性的欲望。
《巴黎记》是诗人于坚对巴黎的朝圣之作。1994年,年届不惑的诗人次飞往巴黎,深夜抵达,他一直以为巴黎是一座璀璨的未来之都,可当黎明唤醒他时,他震惊了。全世界都在追求焕然一新,唯有巴黎岿然不动。这里依然是巴尔扎克的巴黎,雨果的巴黎,波德莱尔的巴黎,这里到处是历史、时间、细节、包浆,这完全是一个旧世界,一个接纳昔日什物、气味的世界故乡。漫步在大街小巷,你感觉高老头随时会从一个漆黑的门洞里出来,贝姨会在某个窗口浇花,你也随时会走进雨果的故居、乔伊斯的故居、马尔克斯落魄时暂住的小旅馆……
此后,诗人经常拜访巴黎,世界日新月异,巴黎我行我素,沉默如大象。二十多年的所见所思,诗人最后熔铸成63段巴黎絮语,163张实地街拍,带你漫游巴黎,寻找全世界的故乡。
《巴黎记》2
1994年秋天,我刚40,第一次离开祖国。
我在机舱里静静地揣着护照,我总是害怕它会飞走。旁边坐着三个形迹可疑的朝鲜人,缩成一团,袋子放在脚下,拉链口子上露出几瓶酒。有人上了飞机,在起飞前的几分钟又被带下去。
那时候,出国就像是一种逃亡,失去了信任,你到国外去干什么?叛国投敌的怀疑笼罩着每一本护照。在海关,士兵声色俱厉地盘问我,哪个单位的?去干什么?除了护照,我还得给他一张同意出国的、盖着红色公章的单位证明。站在那个高高在上的柜台面前,感觉自己是站在一座悬崖边上。
惊魂未定的旅途,直到透过飞机的小圆窗看见下面安静的俄罗斯大地,乌云层叠,森林密集,湖泊遗珠般散落其间,我才确定不疑,安稳下来。
天黑后,我落进巴黎,什么也看不见了,黑沉沉的城,像大地上的星空,有几串星子在移动。旅馆的房间里有巨大的黄色搪瓷浴缸,洪流般的温泉从墙壁里冒出来,其实不过是一只已经磨得有点旧的大号浴缸。那时候浴缸还没有在中国普及。我躺在天堂般的浴缸中,想象着明天的巴黎,那一定是个闪闪发光的地方,矗立着我在电视里见过的那种雄伟高楼、玻璃幕墙,充满着各种尖端设备、电影明星……世界的终端,已经完工的未来,就像那些未来城市景观图所描绘的那样,人们在光辉灿烂的新小区里过着幸福的生活,提着鼓囊囊的购物袋刚刚走出珠光宝气的大商店。
天亮时,打开窗子,外面是一群红顶黄墙的低矮楼房,就像《格林童话》里那些塌鼻子的小矮人,一群麻木不仁的鸽子正在天空飞渡,几乎可以看见地平线,没有什么建筑物高耸入云,有点灰溜溜的,一个旧巴黎。
我觉得自己来到了《格林童话》的某一页里,那些法国民居在我看来就像是宫殿,与我童年时代在《格林童话》里看过的插图中描绘的差不多,安静得惊心动魄,没有人的城市,隐约传来汽车的零碎声音,像是一群刚刚毕业的马蜂。
这个早晨令我崩溃,窗子外面那个旧兮兮的巴黎对我的世界观的冲击,就像一场原子弹爆炸,我的城市正汹涌着一种庸俗不堪的维新思潮,拆得个灰尘滚滚。
20多年前,我秘密地阅读过许多法国文学,罗曼·罗兰、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雨果、左拉、莫泊桑、司汤达、波德莱尔……一边读一边担心着被捕,它们都是“文革”时代的禁书。这种危险的地下阅读,令我比普通的读者更尖锐地进入那些文字,那是吸毒般的阅读,就像一种秘密的逃亡。语言就是存在,我悄悄地越过国家话语的高墙,逃进另一个语言世界,在另一种语言中塑造着另一个我。而就在距离这些秘密读物不过几厘米的地方,随便一张纸都弥漫着那种光明正大的语言:打倒、消灭、阶级、战斗、无往而不胜、正确、伟大……国家太贫乏了,除了标语、口号、语录、社论,没什么可读的,真理沉默如铁,长者守口如瓶,没有任何人会告诉青年关于生命、爱情、人生、奋斗、生活的真理。
我走出旅馆来到街上,即刻进入了巴尔扎克小说的某一章里:青石块铺成的地面,灰黄色的骑楼,贝姨站在窗口浇花,微焦的面包味,苦涩的咖啡味,许多苹果被切开了,那时候苹果非常稀罕,我一年也吃不到一个,香蕉刚刚剥皮,阳台,阳台上的小花园,一只猫在阁楼的窗口蹲着,世界仿佛蒙着一层包浆,停在遥远的一日。我青年时代的某一天,我在梦里来过这里。
转过街角,一个菜市场滚出来,喧哗、新鲜,水灵灵的玫瑰、亮闪闪的鱼、骨头、猪下水、牛肉、葡萄酒、奶酪、大南瓜、百合花、土豆、香肠、金砖般的面包、大胖子、嬷嬷、屠夫、太太、大婶、小姐、老爷子……几个小伙子看见我愣头青般东张西望,就朝我做鬼脸,撇着嘴弄出为婴儿催便的响声。我獐头鹿耳,转身想跑,他们咧嘴大笑。这是外祖母的菜市场。一瞬间,我对巴黎产生了好感、信任。
我一直以为巴黎只是一堆发黄的禁书,或者一个空掉的香水瓶——1966年,许多巴黎瓶子从昆明金碧路的窗子里被扔到大街上,有的香水还没有用光,街道上弥漫着它们奄奄一息的气味。金碧路是一条巴黎风格的街道,20世纪初滇越铁路通车后,陆续盖起来的。
难道巴黎人没有把巴黎拆掉?我一直以为全世界都在追求焕然一新。在最繁华的地带,忽然出现一道两百年前打造的木门,腐朽得就像是一张麻风病患者干掉的脸,狰狞可怖,死亡之门,已经无法开关,只是毫无用处地靠在门口。必须在想象中进出,在想象中转动那已经锈死的黄铜门锁,在想象中穿过阴郁的天井走上楼梯。
我一直被蒙在鼓里,以为求新是一个世界趋势,全世界都在忙着推倒重来。我茫然,我发现巴黎然不动,沧桑大道,到处是历史、时间、细节、包浆、旧世界。一头顽固守旧的大象,趴在世界之夜中。我没有抵达未来,倒仿佛回到了过去。
2011年的某一天早上醒来,我打开窗子,看黎明前的巴黎。楼下面大街的灯亮着,还没有人出现。昏暗朦胧的街角睡着一家人,就像被清洁工遗忘的垃圾袋。几个大大小小的脑袋萝卜般蒙在被子下面,怀着一种无家可归者对世界善意的信任,没有人赶走他们。头顶星空浩瀚,我坐在阳台上,就像一只猫,仿佛刚刚从黑暗的天宇中走下来。
想起我青年时代的朋友老严,30年前他投奔了巴黎,狂
热的工厂左翼青年,崇拜巴黎公社,迷信“生活在别处”“更好的”“未来”。
“文革”一结束就移民法兰西,出了戴高乐机场,拎着行李就去找巴黎公社社员墙。后来在13区结婚,生了一群孩子。我第一次到巴黎,在他家住了一夜,彻夜长谈。他将巴黎视为彼得堡,一个世界革命的中心。后来,终于发现世界是平庸的掩体,巴黎尤甚。法国大革命并没有将巴黎改造成一个崇高的城市,这里不是欧洲的耶路撒冷,没有人要听他用昆明腔的法语朗诵马克思的作品。只有庸常,日复一日的羊角面包、奶酪、咖啡、橙汁、火腿、牛排,像经典绘画一样挂在卢浮宫的墙上。塞纳河畔无休无止的风流韵事,地铁进进出出,按时到站,没有更快,也没有更慢……未来没有出现。挣钱养家的任务繁重,深陷孤独,妻离子散,听说他最后去了诺曼底的海边,在礁石之间不知所终。
老严是一个诗人,以为凭着激情、浪漫主义和一堆时髦的观念就能闯荡世界,最后老家也回不去了,他无法提着一只仅装着几件旧衣服而不是巴黎香水的箱子回老家,衣锦还乡是流亡者的紧箍咒。
我离开巴黎的时候,天光渐亮,一座教堂蒙蒙地出现了,云挡着它的尖顶。一辆黑色小汽车缓缓地驶过依然空无一人的街道,就像一辆灵车。
我不是在怜惜老严,我是在怜惜自己,虽从未离开昆明,我也丧失了故乡。老昆明灰飞烟灭,新昆明加深了我的无根感,令人更痛楚。老严的根在他揣着一本护照登机之后就被斩断了,我的根让我自己眼睁睁地看着它一点点被拔除。
扫描下方二维码直接登录“太图之声”手机版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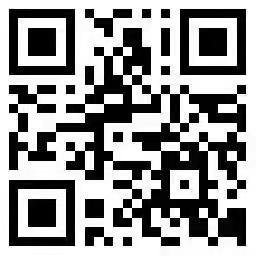
往期回顾:2022年太图之声









 返回顶部
返回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