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图之声(第1055)▏馆员讲书《巴黎记》5(可以听哦!)
2022年05月06日 16:49:17
编辑撰稿人
洪霞
太原市图书馆信息部馆员
播讲人
黄丽萍
太原市图书馆数字资源部馆员
作者简介
于坚
1970年开始写作诗歌、散文、小说、评论至今。
1980年开始摄影至今。
1992年开始拍摄纪录片至今。
著有诗集、文集多种。获数十种诗歌奖、散文奖。
长篇散文《印度记》获2012年《人民文学》杂志非虚构作品奖。
在第十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中,荣膺“2016年度杰出作家”。
纪录片《碧色车站》入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银狼奖单元。
系列摄影作品获2012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华夏典藏奖。
纪录片《同饮一江水》总撰稿。
最近二十年为《中国国家地理》《华夏人文地理》《旅行家》等刊物特约撰稿人。
在国内外多次举办摄影展。
内容简介
到巴黎去,这是一种世界性的欲望。
《巴黎记》是诗人于坚对巴黎的朝圣之作。1994年,年届不惑的诗人次飞往巴黎,深夜抵达,他一直以为巴黎是一座璀璨的未来之都,可当黎明唤醒他时,他震惊了。全世界都在追求焕然一新,唯有巴黎岿然不动。这里依然是巴尔扎克的巴黎,雨果的巴黎,波德莱尔的巴黎,这里到处是历史、时间、细节、包浆,这完全是一个旧世界,一个接纳昔日什物、气味的世界故乡。漫步在大街小巷,你感觉高老头随时会从一个漆黑的门洞里出来,贝姨会在某个窗口浇花,你也随时会走进雨果的故居、乔伊斯的故居、马尔克斯落魄时暂住的小旅馆……
此后,诗人经常拜访巴黎,世界日新月异,巴黎我行我素,沉默如大象。二十多年的所见所思,诗人最后熔铸成63段巴黎絮语,163张实地街拍,带你漫游巴黎,寻找全世界的故乡。
《巴黎记》5
巴黎诗歌之家,在蓬皮杜中心附近的莫里哀小巷里,这是一条18世纪的小巷,石头铺的路面,几分钟就可以穿过去另一条街。
小巷里有一家首饰店、咖啡馆和一家卖母亲和祖母穿的漂亮衣服的小店,时装不仅是青春的,也是熟透的、稳重的、老迈的。稳重朴素的时尚而不是轻浮的时尚,这才是巴黎。
白发苍苍涂着口红的老妇躅蹐而来,站在玻璃窗前看那些令她动心的裙子,她看了一阵子,没进去,而是转过身进了诗歌之家,她是来听我朗诵诗歌的。这个下午,谁家在烤面包,面包香在小巷里弥漫着,就像我少年时代那些金色的下午,外祖母的下午。
她总是在下午3点左右出门,穿过铁局巷,穿过坐在人行道上一个接一个的货郎,有个来自宜良县的农民在卖荷花,她走去电影院旁边的燕鸿居吃一碗红油水饺。那馆子里可以听见有人在唱滇剧,拉二胡,随地吐痰。
巴黎的这种下午从未被改动过,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生活一直在继续,即使在德国人占领巴黎的时代,沙龙、时装、烤面包、卢浮宫或者先贤祠也从未停止。抵抗的抵抗,喝咖啡的喝咖啡,打架的打架,这就是巴黎,根深蒂固的多元之都。就是1968年的革命,也并非全城出动,站在阳台上观景并不会被视为可耻,选择而已,这就是巴黎。
这条小巷连接着两条街,这头热闹非凡,一家接着一家的咖啡馆、酒吧,沿街都是无所事事坐着边看街景边喝着什么的闲人,那头却冷清许多,摩托爆炸般地疾驰而去。二楼的窗帘后面,有时候出现一位走到窗口来接手机的青年。手机在巴黎有点自惭形秽,接手机的人总是要道歉,很不好意思地捂着它溜到一边去接。基本看不见手机,它们躲着。
诗歌之家里面有个半圆形的小剧场,可以坐五六十人。还有一间客厅,来访巴黎的世界各地的诗人经常在此聚会。我将在这里朗诵《0档案》片段和其他诗。入场要买票,5欧元。我的3部法语诗集已经排列在入口的桌子上,朗诵会将由诗人米歇尔·德吉主持。
3点,德吉来了,我们一见面就彼此认出。他还在感冒,穿着黑色的大衣,围着一条灰色的羊绒围巾,戴着助听器,满面沧桑。
德吉80岁,俨然是巴黎诗歌的教父,在法国诗坛一言九鼎(有人这么评论他)。阿尔及利亚诗人安敏也从首都阿尔及尔赶来,我们在哥伦比亚的麦德林诗歌节相识,他说他要来巴黎参加我的诗歌朗诵会,居然真的来了。
尚德兰,小巧玲珑的妇人,第一次见面,她翻译的我的诗集《被暗示的玫瑰》刚刚出版。还有许多巴黎的文人,写诗的、画画的、记者……朋友为我介绍了几个,都记不住名字。活动包括两部分,朗诵和讨论。我先朗诵汉语,然后其他人朗诵法语。高度安静,人们在黑暗中听着。西方语言与汉语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没有字,字母是可以只闭上眼睛听的,汉字不行,你得看,如果他听不清,还要书空,这是汉语特有的学习汉字的行为,小学上课时,老师教每个字,我们都要用手在空气中书写这个字,横竖撇捺……。
如果像兰波那样注重声音,诗只有简单化。
这是哪一个字?这是汉语最基本的问题。
声音可以将兰波带出上帝的管辖。横竖撇捺无法突破,徐冰的尝试只是恶作剧。拼音没有字的限制,因此说话发音一定要准确,发音不准就是文盲。汉语则允许含糊其辞,字写清楚就行了,不能有错别字。这种朗诵会太一本正经了,有点干巴巴的,诗歌是一个个文本对象。中国的朗诵会以玩为主,诗次之。大家更愿意看字,朗诵现场主要是用来交际的。
我们来到蓬皮杜艺术中心旁边的一家酒吧,德吉点了葡萄酒、鹅肝酱、奶酪和小饼干。隔着玻璃窗可以看见蓬皮杜艺术中心前面的广场,许多波西米亚人或者装成波西米亚族的人躺在那里,那块巨大的广场,自建成以来,就一直是世界各地前卫艺术家们的毯子。
德吉说,他写作没有规律,有时候他睡觉时突然爬起来写一点,然后继续睡。他说他今年又写了一本诗。这个下午,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音乐会、剧院、酒吧、电影院、展览馆、美术馆、沙龙、咖啡馆进进出出,每时每刻,巴黎都创造着歌剧、音乐、电影、绘画、舞蹈、戏剧、诗歌等等,一个塞纳河畔的巨大的艺术作坊。它的作者一个是看不见的时间,另一个是那些赶来巴黎写点什么的人们。
巴黎比昨天更接近巴黎。
莫里哀小巷的诗歌之家只是巴黎无边无际的艺术碎片中的一片,几十个人的聚会而已,就像那些19世纪老楼中的某扇窗子,被阳光瞬间击中,亮了一下,又迅速回到黑暗中。
巴黎的魅力就在于它热爱光明也不拒绝黑暗,天堂与地狱共存一区,彼此交融,巴黎永远也不会驱除钟楼怪人,他的存在是天使的人性根源。阴阳交错在两极之间保持着一个巨大的“之间”。黑暗并非必须清除的负面力量,黑暗也构建着巴黎的魅力。
巴黎创造了某种叫作巴黎的东西,某种场,或者叫作巴黎矿,就是摧毁了巴黎本身,这种巴黎矿也不会消失,这种矿物质已经成为超验,蔓延在人类的欲望中。
“到巴黎去”,这是一种世界性的欲望。
你想成为一个另类之辈,那么到巴黎去,就像杰克·伦敦小说中的育空,吸引着世界的人生淘金者。就像20世纪初的圣彼得堡或者20世纪30年代的延安吸引革命者那样,巴黎吸引着世界上那些崇拜“艺术形而上”的人们,“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吸引着世界上无数的想成为诗人、思想者、艺术家的人们。巴黎不在乎你物资匮乏,或仅仅因为精神空虚而闲逛,巴黎愿意满足你的安贫乐道。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闲哉,回也!”(《论语》)
巨大的精神之邦,现实的空间日夜生发着无用的空间,想象的巴黎和现实的巴黎交错,穿过巴黎,就是穿过波德莱尔所谓的“象征的森林”,巴黎并不要求你多么富有,只要有基本的温饱,你就可以得到那种财富永远购买不来的富足感。巴黎吸引着一条条满载着难民的醉舟,他们的受难是一种精神的受难。人们涌向巴黎,有时候只是为了一睹卢浮宫的《蒙娜丽莎》。
似乎荷尔德林的那句诗——“人充满劳绩,却还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并没有那么深刻,它只是为巴黎这种地方写下的一句平庸广告。
这是一个另类的巴黎,我们所憧憬的巴黎,虚构的巴黎,已经辞世的巴黎,或者是我所愿意居于其中的巴黎。
也许真有这个巴黎,也许没有。
扫描下方二维码直接登录“太图之声”手机版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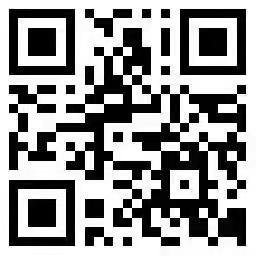
往期回顾:2022年太图之声









 返回顶部
返回顶部

